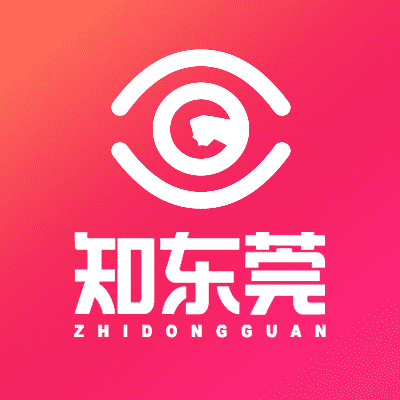
央媒接连发声批评!始祖鸟海内外道歉信被指“双标”,最新回应
9月19日,户外品牌始祖鸟联手艺术家蔡国强在喜马拉雅山放烟花引发争议。
21日,始祖鸟、蔡国强工作室在社交平台发布致歉信,同日,始祖鸟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也发了英文致歉信,不过内容与国内版本有差异,相关话题登上热搜。

国内版道歉信中,始祖鸟表示,在对艺术表达边界评估要更专业、对自然要更谦卑,承诺在政府监管下,配合团队复核项目生态影响,邀第三方评估并依结果补救,同时推进藏地环保计划与文化公益项目。

海外版称,对青藏高原烟花表演深感遗憾,此行为与品牌环保价值观及期望不符,郑重致歉。同时,还提到“正与相关艺术家和中国团队沟通,调整工作方式避免类似情况”。

部分网友质疑,始祖鸟的致歉“不够诚恳”“内外有别”,文中提到的“与中国团队沟通调整工作方式”有“甩锅”的嫌疑。
对此,始祖鸟品牌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,暂不知悉此事的详细情况:“有相关问题可以向公告中提及的邮箱反馈。”
央媒发声批评“喜马拉雅山烟花秀”
21日,新华社、人民日报接连就“烟花秀”发声。
新华社发文《致敬自然,无需烟花证明!》评论此事:当一片片烟花于轰鸣声中从山脊间升起,炸开的不仅是彩色烟雾,更是商业逻辑与生态伦理的激烈碰撞。这场争议暴露出的深层次矛盾,值得全社会共同反思:我们是否需要这种烟花秀来“致敬自然”?真正的敬畏,从不是在人间净土搞行为艺术,而是学会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和沉默。
随后,新华社再发评论《放错了地的“烟花秀”,再美也是破坏》。评论连发两问:如此一场声势浩大的烟花秀,相关燃放材料是否按照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承载力进行过评估?相关部门在层层审批中,是否始终秉持对破坏生态环境“零容忍”的态度,“坚持生态保护第一”的原则是否仍悬在心间?
人民日报也发文《烟花散去,不能仅留下道歉》指出:环保与艺术并不对立,完全可以相得益彰,关键是要有合适的尺度和规范。真正的艺术,应当尊崇真善美,敬畏自然,抚慰人心,而不可伤害自然界。而商业化的参与,更应有规矩和界限,倡导正向善意的价值,不可只图哗众取宠。烟花散去,留下的不能仅是道歉,更应是保护生态的行动。
蔡国强烟花秀玩“炸”了,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“生态艺术”?蔡国强作为以烟火秀闻名的艺术家,为何此次创作遭遇如此巨大的争议?艺术与自然的“对话”,应如何守住生态伦理的底线?独立策展人、艺术批评及理论研究者李裕君就此接受记者专访,并对事件进行深入解读。
记者:大地艺术是不少当代艺术家青睐的创作方式,过去是否也存在类似《升龙》这样的争议和问题?
李裕君:大地艺术(Land Art)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,艺术家将创作现场移至荒漠、海岸、山地等未被驯化的自然空间,试图打破艺术与生活、人工与自然的边界。然而自诞生之初,这场看似“回归自然”的艺术运动,其实就埋藏着深刻的生态悖论:它既以自然为灵感源泉与表达载体,又往往以“改造”,甚至“干预”的姿态介入自然。
早在1970年,罗伯特·史密森的《螺旋形防波堤》就引发过类似争议。艺术家将6000吨玄武岩与泥土倒入犹他州大盐湖,构建出直径150米的螺旋状结构,不仅改变了盐湖的局部地貌,其材料运输和机械作业过程也对周边土壤与水体造成扰动。

罗伯特·史密森(Robert Smithson)的《螺旋形防波堤》。
在我看来,这种艺术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延伸。他们并非真正将自然视为与人类对话的“主体”,而是用来承载艺术家观念的“空白画布”。蔡国强的《升龙》项目正是这一基因悖论的当代延续。这类大型艺术项目究竟是“艺术与自然的共情”,还是“以艺术之名的生态消耗”?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。
记者:项目方强调初衷是“致敬自然”,使用“生物可降解烟花材料”,为何适得其反引发如此巨大争议?
李裕君:表面上看,《升龙》项目用“瞬时性”的烟花替代了传统“永久性”的大地艺术,似乎减少了对自然的长期占用。但其实生态影响不是“可降解材料”就能完全消解的。喜马拉雅山区属于高寒草甸生态系统,植被恢复周期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。项目实施过程中,大规模团队进驻也会直接破坏表层土壤与草本植被。这种破坏对脆弱的高寒生态而言,可能是不可逆的。

蔡国强在喜马拉雅山脉海拔5500米处实施的烟花项目《升龙》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,《升龙》的“崇高性”表达,恰恰建立在对自然“稀缺性”的消费之上。艺术家选择在人类活动极少、生态极脆弱的区域创作,本质上是利用自然的原始纯净烘托艺术的“震撼力”。这种将“世界屋脊”降格为“画布”、将自然的“生态价值”转化为艺术的“审美价值”的行为,是与“生态艺术”的名义背道而驰的。
记者:背后商业机构的参与也是这次艺术项目的争议点,这是否改变了“生态艺术”的性质?
李裕君:大地艺术的初衷本来是反对艺术商业化的,它的早期创作规模有限,尚未深度卷入资本逻辑。然而,随着当代大型环境艺术项目对技术、人力、场地的需求越来越高,不得不依赖雄厚的资本支持。这次《升龙》项目与国际户外品牌的深度合作正是典型例子。
这种合作模式也重塑了艺术的创作逻辑。资本的介入早已不只是纯粹的“资金支持”,更成为左右艺术选题、形式与传播的核心力量。《升龙》项目的合作品牌希望通过“喜马拉雅”等标签塑造“高端、环保”的品牌形象,进而推动产品销售。“生态艺术”就逐渐异化为资本的“绿色营销”,沦为商业目标实现的“文化工具”,而不再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。
记者:您认为“生态艺术”应当如何重新定义自身边界?
李裕君:我们需要重新定义“生态艺术”的核心:它不应是人类对自然的“改造”或“消费”,而应是人类与自然的“共生”与“共情”;不应追求表面的“环保符号”,而应践行实质的“生态责任”。
真正的“生态艺术”应建立在“低影响、修复性、社区参与”的原则之上。以《升龙》项目为例,蔡国强应放弃生态脆弱的高海拔山区,转而选择生态系统更稳定、人类活动影响已存在的区域,同时避免大规模场地干预,选择更低碳的表达形式。唯有如此,才能真正减少项目的生态足迹,让艺术不再成为自然的“负担”。

蔡国强在喜马拉雅山脉海拔5500米处实施的烟花项目《升龙》。
此外,《升龙》项目也应将“生态修复”作为核心环节:在实施前联合生态学家制定详细修复方案,在实施后长期监测当地生态状况,弥补生态影响。实际上,修复过程本身可以成为艺术的一部分:通过记录修复过程,制作纪录片或装置作品,让观众关注“生态修复”的长期性与重要性。
记者:这次争议对未来的“生态艺术”创作有何启示?“生态艺术”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与自然的对话?
李裕君:这次争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。当代“生态艺术”若要真正承担起伦理责任,就必须放弃“崇高化的自我表达”,转而拥抱“谦逊的生态实践”;必须放弃“资本驱动的风险转嫁”,转而追求“社区参与的公正共生”。
“生态艺术”的终极目标不应是创造“震撼的景观”,而是重建“人类与自然的情感联结”。唯有如此,生态艺术才能真正实现与自然的“真诚对话”,在生态危机的时代为人类提供一种“可持续的审美方式”。艺术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生态保护的力量,在人类与自然之间构建起一种基于共情与共生的新型关系。这才是“生态艺术”真正的伦理内核,也是它在未来应当坚守的方向。
赞
2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