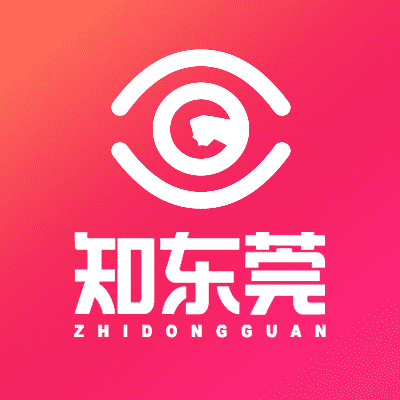
930年前,苏东坡看到的东莞、惠州、归善古城是怎样的?
东坡于绍圣元年(1094年)至四年谪惠,经停过东莞县城,长住惠州府城和归善县城(今惠州市惠城区)。与他密切相关的这三座古城,当时分别是什么情形?或者说,930年前东坡看到的这三城是怎样的?现作一简要考证。
东莞县城
一、人口3000名左右
当时东莞县城人口,目前暂未查到史料记载,推测3000人左右。
宋承唐制,县分等级,不过在七等之外增加了次赤、次畿和中下三个等级。其中,赤、次赤、畿、次畿、望、紧六级县,主要依据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地位,并结合人口数量确定;上、中、中下、下四级县,主要依人口数量和地理位置确定;1万户以上者为望县,7000户以上者为紧县,5000户以上者为上县,3000户以上者为中县,不满3000户者为中下县,1500户以下者为下县。每三年考核升降一次。(注1)
东坡在绍圣三年一月写给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司程正辅的信说:“博罗正月一日夜,忽然失火,一邑皆为灰烬,公私荡然……百姓千人,皆露宿沙滩,可知!”(注2)博罗定为中下县(注3),则总户数不足3000户,如按平均每户4-4.5人计,则全县总人口不足1.35万人;住县城百姓约千人,则是约占县总人口10%。
明崇祯《东莞县志》明确记载,唐代和元代,东莞县定为中县,宋代为何等无记载(注4)。
如按中县上限4000户、平均每户4-4.5人计,则当时全县总人口约1.6-1.8万人,如10%住在县城,则有1600-1800人左右。
如按上县的上限7000户、每户4.5人计,则全县3.1万人,如10%住在县城,则约3000人。
如按广州下属8县平均每县17907.63户、每户4-4.5人计,则全县7万-8万人,10%住县城,则有7000多人。
当代人口高密度城市,每平方公里一万人,容积率2.0、人均100平方米住宅面积。考虑到宋代县城只有0.45平方公里,容积率不到1,人口总量不应超过4500人,故取3000人左右这个中间数。
二、滨海城市
唐肃宗至德二年(757年),宝安县更名为东莞县,县治迁至“到涌”(今莞城),此后未曾变更。
宋代县城在原土城基础上改筑为砖城。明崇祯《东莞县志》记载:“邑之旧城,砖砌。东南循到涌为城,即今放生桥壕是也(放生桥,即德生桥,在东莞中学南校区与东莞宾馆之间的市人民公园门楼内侧)。”(注5)
推测当时城东门在今东门路、东正路路口,西门在今市桥,南门在今人民公园德生桥位置,北门位置不详,总面积约0.45平方公里。
黄旗山之余脉,延伸至城内东北角,名为壬峰,县衙背依此峰,坐北朝南,城东边以癸水为护城河,南边、西边均以到涌为护城河;西北有水系联通东江南干流,南边有水系联通狮子洋。
据赵凡夫《从东莞诗词看宋以来莞城的水陆变化》(注6)考证:在宋代,今东莞宾馆停车场、新华书店、草塘、金牛路、戴屋庄、鸭仔塘一带,仍是海洋;东莞中学南区的南端,还是一片沼泽。所以,宋代建城墙不包制高点钵盂山、道家山于城内。
1966年东莞博物馆对镇象塔进行了发掘和迁移。当时,石塔露出地面的只有部分石幢柱,高约106厘米。深挖之后发现,塔下并无象骨等遗物遗存,反倒有比建塔时间晚116年的“元丰通宝”铜钱,石廓底下0.88米以下为纯黄色沙子,是未经任何扰动的海沙堆积层,说明南汉大宝五年(宋太祖建隆三年,962年)兴建资福寺、筑镇象塔之时,寺址(今莞城中心小学)之前一百米左右,仍为海边,不便立塔。过了一百多年以后,到元丰年间,今象塔街34号一带已经淤成陆地,莞人才将象塔向前移置至此。
据以上情况可知,当绍圣元年(1094年)东坡贬惠州,路过东莞之时,县城实为滨海城市,县城南边以到涌为护城河,登上南城门楼可见护城河堤之外数十米处,以及今草塘、金牛路一带,仍是一片汪洋大海。
道家山,在莞城西南隅。上有上清观,旧址在今之市工人文化宫所在。据明邓云霄《凤凰台诗社重修记》记载,上清观传说建于梁武帝时期(503-548年),北宋政和四年(1114年)县令改建,立三清像。观左有雁塔,始建于南宋淳祐年间(1241-1252年)(注7)。依据前文考证和现今地势分析,推测道家山,其东北面与县城隔浅海相望,其西南面绵延经现今莞城政府楼址至红山一带,再到蚝岗一带,形成一脉低山岗地,是古人滨海而居的好地方,所以先有5000年前的蚝岗贝丘遗址,后有梁武帝时期兴建的山顶道观,再有政和四年改建之事,可以采信。
据此推测,政和四年之前20年东坡经过东莞之时,道家山“凤凰台上金鸡叫”之名景,当时已经出现。

三、莞人轻施乐舍
宋代东莞人,“轻施乐舍,甲于四方”。其依据,参见东坡元符三年十月在广州所写《资福寺罗汉阁记》云:“四方之民,皆以勤苦,而得衣食。所得毫末,其苦无量。独此南越,岭海之民,贸迁重宝,坐获富乐。得之也易,享之也愧。是故其人,以愧故舍。海道幽险,死生之间,曾不容发。而况飘堕,罗刹鬼国。呼号神天,佛菩萨僧,以脱须臾。当此之时,身非己有,而况财物,实同粪土。是故其人,以惧故舍。愧惧二法,助发善心,是故越人,轻施乐舍,甲于四方。
东莞古邑,资福禅寺,有老比丘,祖堂其名。未尝戒也,而律自严;未尝求也,而人自施。人之施堂,如物在衡;损益铢黍,了然觉知。堂之受施,如水涵影;虽千万过,无一留者。堂以是故,创作五百,大阿罗汉,严净宝阁。涌地千柱,浮空三成,壮丽之极,实冠南越。”(注8)
四、人象之争
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政权曾组建以战象为核心的特殊作战部队,可见当时野象数量较多、有象可驯。
南汉大宝五年(宋太祖建隆三年,962年)秋天,莞城郊外野象成群,踏食田禾,民苦无奈。南汉官府禹余宫特使邵廷琄组织捕杀,烹肉赡军,聚骨埋地,在资福寺之前建造
了石经幢(俗称镇象塔),镇压野象,超度象魂,并在塔上刻文记录此事。(注9)
宋开宝六年(973年)开始,朝廷禁止岭南诸州民捕猎野象(注10),但落实不力。宋淳化二年(991年),曾知广州的李昌龄上书皇帝说:“雷、化、新、白、惠、恩等州山林有群象,民能取其牙,官禁不得卖。自今宜令送官,以半价偿之,有敢隐匿及私市与人者,论如法。”诏从之。(《宋史·李昌龄传》)
到东坡路过之时,东莞县已经多年不见野象踪迹,野象已退缩至粤北山区、西江谷地等处。
不过,邻近的惠州府境内仍有野象活动。北宋官员唐庚(1069-1117),在政和元年(1111年,即东坡离惠之后14年)至五年贬官于惠州,期间写有《射象记》一文,生动记载了惠州历史上一次人象冲突事件:政和三年(1113年)三月,一头野象闯近惠州城北门,数百人手持戈戟、弓弩等围攻,监税官蒙顺国一人盲目逞勇被象踩踏身亡,因缺乏统一指挥,旁观者溃散,野象负伤逃走。
五、盐业兴旺
宋代东莞有靖康、大宁、东莞三大盐场,盐业生产销售兴旺,是岭南盐业重要生产基地。据北宋元丰年间(1078-1085年)《元丰九域志》记载,东莞盐场隶属广州盐仓管辖,实行盐丁制役使灶户。
据《靖康谱》记载,西晋元康元年(291年),茅洲河流域河口以南的海岸,南到福永,设置了归德盐栅;北宋后期,归德盐栅升格为盐场;南宋时,归德盐场衙署在沙井衙边村附近,该村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南宋嘉定十三年(1220年)、盐大使周穆所建龙津石塔,是深圳现存最早的地面建筑物。元、明两代,归德盐场是广东十三大盐场之一。清初,归德盐场因禁海迁界盐课司衙署被破坏。乾隆三年(1738年),东莞县的靖康场产盐日少,由归德场大使兼理,归德场遂改名归靖场。乾隆五十四年(1789)归靖场、东莞场全部裁撤,实行改埠为纲,盐田池漏拆毁净尽,养淡改作稻田。
惠州府城
一、人口约2万名
惠州府城人口,暂未查到史料记载,推测约2万人。依据:
一是惠州府总人口约20万人。据《宋史·地理志》记载:宋元丰年间(1078-1085年),惠州4县,共61121户(注11),按每户4-4.5人计,共约24.4万-27.5万人;按10%住在府城计,则有2.4万-2.7万人。
另据《元丰九域志》记载:宋元丰三年(1080年),惠州4县,原籍25434户、客籍21558户,共46992户(注12),按每户4-4.5人计,则有18.8万-21.1万人;按10%住在府城,则有2万人左右。
二是绍圣二年惠州驻兵约1000人。当年五月,东坡致程正辅信(第三十首)说:
“今且体问得逐营事件如后:
一、本州管澄海两指挥,禁军皆有营房,不外住。(略)
清化指挥见管二百三十人,只有官屋三十间(略)
牢城指挥见管二百六十人,只有官房四十间(略)
泉州客军一百五人,并无营房(略)
信州客军九十六人,见管营房七间(略)
广州客军九十人,不曾与置营房(略)
……如惠州兵卫单寡,了无城廓,奸盗所窥,又若营房不立,军政堕坏,安知无大奸生心乎?”(注13)
据此信统计,当时驻惠州官兵合计近1000人。如按兵民比例1:20计,约有2万住民。
三是东坡当年有文说“鹅城万室”。绍圣三年(1096年),东坡在白鹤峰购地建屋,新屋上梁时写就《白鹤新居上梁文》云:“鹅城万室,错居二水之间;鹤观一峰,独立千岩之上。海山浮动而出没,仙圣飞腾而往来。”(注14)此所谓“鹅城”,是惠州之别称。“万室”,意即“万户”,按《文献通考》卷十一《户口考》,北宋元丰三年官方记载,广南东路有565534户、1134659口,户与口之比为2.01。按此比例计,“万室”即2万人左右。东坡是官员,应该能够得知所住地惠州官方的人口数字,笔下所记不会相差太远,故此数可信。如按每户4-4.5人计,则有4万多人,可能过多,对此可理解为东坡写诗,以“万室”泛指人多,并非实数。
二、滨江临湖城市
隋朝开皇十年(590年),循州总管府治从龙川县,迁至归善县梌木(即枫木)山。自此,成为后来历代州府级治所。至宋代,惠州府城初具规模,傍丰湖(今西湖)而建,开有东、西、南、北4门,周长约2里。
州、县两城隔江相望。在西枝江和东江的交汇口,苏东坡倡建了东新浮桥,惠州府城位于其西边,归善县城位处其东边。
合江渡,是宋代梌山东南麓、惠州府城小东门外的一个渡口,是惠州对外交通的主要水路通道,也是官员往来和吏民进出的重要途径。当年东坡乘船抵达惠州府城,应是在合江渡上岸,之后暂住合江楼。
合江楼,在郡衙之东几十米处,是北宋惠州府城专门接待广南东路最高级官员——经略安抚司(俗称帅司)、转运使(俗称漕司)、提点刑狱司(俗称宪司)、提举常平司(俗称仓司)的官办宾馆,也是他们的临时衙门。苏东坡在惠州期间得到州守詹范和宪司程正辅的关照,曾两度在合江楼居住。这里可以饱览“海山葱昽气佳哉,二江合处朱楼开”之胜概,享受“江风初凉睡正美,楼上啼鸦呼我起”(《寓居合江楼》)之惬意,感受合江楼下“歌呼杂闾巷,鼓角鸣枕席”(《和陶移居二首并引》)之市井气息。
所以,东坡寓惠之时,惠州府及归善县城,都是滨江临湖城市。
三、言语不通
苏过《次陶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》云:“岁丰田野欢,客子亦少休。糟床有新注,何事不出游。春云翳薄日,磻石俯清流。心目两自闲,醉戗不惊鸥。茅蒋谁氏居,鸡鸣隔林丘。曳杖叩其门,恐是沮溺俦。但苦鴃舌谈,尔汝不相酬。筑室当为邻,往来无惮不。澄江可寓目,长啸忘千忧。傥遂北海志,馀事复何求。”
其中,“但苦鴃舌谈,尔汝不相酬”,意即苏氏父子与当地人之间语言不通、难以交往。推测只有其中的北方近期迁居者、地方上层士绅,与他们能以官话相谈。
唐代韩愈曾贬阳山县令,在《送区册序》中有说:“言语不通,画地为字,然后可告以出租赋,奉期约。”与韩愈的这种情形相比,东坡父子当时语言沟通的困难虽然犹在,但是应该小很多。
归善县城市井寥落
归善定为中县,户数在3000至5000户之间,县治位于府城之外,江水之东、白鹤峰之南,并无城墙,市井寥落,每日止杀一羊。
东坡借住的嘉佑寺,位于归善县治东侧,极为偏僻,东坡《和陶移居二首并引》诗云“昔我初来时,水东有幽宅。晨与鸦雀朝,暮与牛羊夕”(注15)。
注1:齐子通《宋代县望等级的划分标准探析》,《历史地理研究》, 2021年 41期。
注2:《苏东坡全集》,北京燕山出版社,2009年12月第1版,卷一百《尺牍·与程正辅(七十一首)》之第十八首,第2621页。
注3:《惠州市志》,惠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,中华书局出版,2000年3月第1版,第一编《政区》,329页。
注4:《东莞县志》,明[崇祯]张二果等著,杨宝霖点校,东莞市人民政府,1994年1月重印,卷之一《地舆志·城池》,第20页记载,唐、元皆定为中县。
注5:《东莞县志》,明[崇祯]张二果等著,杨宝霖点校,东莞市人民政府,1994年1月重印,卷之一《地舆志·城池》,第22页。
注6:《东莞诗词俗曲研究》,杨宝霖主编,乐水园印行,2002年5月,第442-462页,赵凡夫《从东莞诗词看宋以来莞城的水陆变化》。
注7:《东莞市志》,东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,广东人民出版社,1995年第1次印刷,第二十二编《文化文物胜迹》,第1152页。
注8:《苏东坡全集》,北京燕山出版社,2009年12月第1版,卷五十九《记·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》,第1563页。
注9:《东莞市志》,东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,广东人民出版社,1995年第1次印刷,第二十二编《文化文物胜迹》,第1159页。
注10:《惠州市志》,惠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,中华书局出版,2000年3月第1版,《大事记》,第19页。
注11、12:《惠州市志》,惠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,中华书局出版,2000年3月第1版,第三编,《人口·人口规模》,第439-450页。
注13:《苏东坡全集》,北京燕山出版社,2009年12月第1版,卷一百四《尺牍·与程正辅(七十一首)》之第三十首,第2625-2626页。
注14:《苏东坡全集》,中华书局出版,卷一百五十六。
注15:《苏东坡全集》,北京燕山出版社,2009年12月第1版,卷四十诗集,第1013页。
赞
0